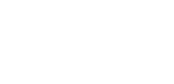109年前的今天,京师图书馆在北京广化寺正式开馆接待读者,它就是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汇聚了古今无数智者思想的书页空间里,似乎蕴藏着世间古往今来的秘密。这些秘密原本只为少数人所知,因为图书馆的存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触手可及。
伴随着书籍形态的变迁,曾经以庙宇、楼阁、超大建筑存在的图书馆实体,也可以幻化成数字图书馆——即便如此,图书馆的故事也还远远没有结束。
藏书楼少数人的智库
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图书馆就是进步阶梯搭建的殿堂。图书馆的萌芽起源于何时?这恐怕要回到书籍最开始的模样去寻觅。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尚书·多士》里的一句话,阐明殷商的先人已经有了册典。册典就是简书,更确切地说,是以甲骨文形式保存的书籍。殷商的甲骨文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文字体系(迄今已发现4000多个单字),甲骨典籍的留存数量也相当丰富,因此有观点认为,我国图书馆的起源应追溯至殷商时代。安阳殷墟是我国最大的甲骨文发现地,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的窖穴里,共计出土甲骨约15万片。甲骨片上篆刻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商代社会祭祀、狩猎、农业、天文、军事等方方面面,完全能担当起图书馆的雏形。
而在殷商时代结束后的三百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也建立起了一个图书馆。亚述帝国的亚述巴尼拔二世曾广泛搜集几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语言的古代文献——亚述语、苏美尔语、古阿卡德语、乌嘎利特语和阿拉米语,汇聚到首都尼尼微的一栋建筑里。不同于殷商的甲骨,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书是泥板书,或者称陶土书。各种印在泥板上的著作被分类捆扎得整整齐齐,有标签提示其上的内容,另有分类目录记录每个著作的标题以及泥板数量。亚历山大图书馆莎草纸在火中俱焚,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泥板书却有相当部分都被完整保存了下来,迄今仍有两万块泥板书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
书籍,承载着历史、知识与思想,拥有数量众多的藏书,也是一种垄断。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从我国西周时起,就有专司管理古籍,以及专存古籍的建筑如“故府”和“盟府”;秦统一六国后,特设“柱下史”的职位专管藏书,专门的藏书地点安置在咸阳阿房宫的“秘书阁”;到了汉高祖刘邦的时代,皇家图书馆已经扩充为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按照《隋志》的说法,到了汉成帝时,藏书数量已达“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
汉代发明的纸张,意味着纸质书籍的保存相较于之前的甲骨、简牍、金石或缣帛,更节省储存空间,而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则大大提高了书籍的数量——唐太宗的“弘文殿”里,藏书已达二十余万卷,负责管理的“秘书监”执掌重权。此外,无论是宋代“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文献通考·经籍考》”的“崇文院”,还是明代“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的“文渊阁”,以及清代四库全书编纂完成时,专门修建的“四库七阁”(七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都是皇家的藏书机构。
除了官府的“文阁”,藏书机构还散落于寺观、书院以及私人空间。公元550年,四百二十万字的佛经收藏出现在湖南房山的石柱和洞窟墙壁上,类似这样的“石刻图书馆”或者说“石林”,可以系统地收藏和保存经典的石刻文本。而私人图书馆,则散见于明代“天一阁”“汲古阁”与“澹生堂”等私人藏书楼,以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和“嵩阳书院”等四大书院里。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藏书楼,一个“藏”字,都说明这些书大多被藏之于楼,束之高阁,只有少数人能够触碰、阅读。鉴于书籍宝贵,即使私人藏书也吝于示人。明代藏书家叶盛所写的《书橱铭》就有:“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了,惟学斅(音xiào),借非其人亦不孝。”
在西方,图书馆大部分时候同样成为上层阶级知识垄断的智库。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时曾作为博物馆、翻译所,以及各国学者的工作室。学者研究期间的开销由托勒密官方负担,相应的,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要留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里。为了巩固图书馆的王室控制,托勒密王室指示所有到访这座城市的人们所携带的书籍,都要先送交图书馆复制,他甚至还命令禁止出口莎草纸。亚历山大图书馆里的藏书曾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圣经旧约》的希腊文本,《伊利亚特》的手稿……无论东西,图书馆所藏有的知识都曾是一种少数人孜孜以求和尽力储藏的智慧资本。
公共图书馆面向民众开放启迪民智
第一座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头衔或许应该授予科西莫·德·美第奇在1444年建造的圣·马可图书馆,它的出现打破了欧洲社会修道院图书馆长期垄断知识传播的局面。美第奇家族的崛起正值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统治者柯西莫·美第奇和其孙洛伦佐·美第奇建立的美第奇家族图书馆,藏书里不仅包含宗教类书籍,还囊括哲学、史学、诗歌和语法类等人文类别。图书馆既允许学者们到馆内阅读,也欢迎其他藏书家到馆内抄写珍本书籍,由此逐渐从私人图书馆转变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从这时起,图书馆不再只是为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服务,而是面向民众开放。可以说,美第奇家族图书馆促进了人文主义理念的传播,担负起了文艺复兴学术平台功能,图书馆也因此注入了除智库以外新的内容。
1627年,法国巴黎马萨林图书馆馆长诺代在其所著的《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意见》一书中,设想了一个完美的科学研究图书馆的雏形,其核心思想是:图书馆不应该专为特权阶级服务,必须向一切研究人员开放。16世纪上半叶的马丁·路德也有同样的倡导,即德意志的城镇图书馆应该为一般市民服务。近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的英美两国:185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公共图书馆法,到1900年英国有公共图书馆360所。1848年美国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在波士顿市建立公共图书馆的法案后,各州也纷纷通过公共图书馆法,其中纽约公共图书馆逐渐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依法设立、经费来源于行政机构的税收、向所有居民开放,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共同特征。
中文里的“图书馆”出自日文“図書館”,1896年9月,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时务报》上刊文,首次使用了“图书馆”一词。而“图书馆”一词第一次被官方文件正式采用,是在1904年清政府颁发管学大臣张百熙制定的高等教育纲领《奏定大学堂章程》里——“大学堂当置附属图书馆一所……”1898年京师大学堂一成立,即有藏书楼的设置。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建,藏书楼得到迅速发展,且不久即改称图书馆,这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图书馆。
1910年5月,武昌文华公书林成立,秉持建立“一所不仅供学生用也供大众用的图书馆”的理念,旨在启蒙民众,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诞生。
1909年9月9日,清政府批准兴建京师图书馆,馆舍设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广化寺。然而直到清帝逊位之日,京师图书馆始终没有正式接待过读者。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并将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它就是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20世纪初,随着各省相继成立图书馆,图书馆的名称开始在社会上通行。
数字图书馆海量电子化信息穿越时空
1984年,美国学者K.E.道林在其所著的《电子图书馆:前景和进程》中最早提出了数字图书馆(当时称为电子图书馆)的概念,彼时还是局域网和城域网的时代,但图书馆的崭新形态已经足够让人激动。1992年,美国联邦政府发布了《信息基础建设与科技法案》,首次以法案形式界定了数字图书馆的含义、功能和技术应用的范围,欧洲各国政府紧随其后,接着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也相继投入开展本国的数字图书馆开发。
我国对“数字图书馆”的开发开始于1995年,这是一个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参与的数字图书馆应用型项目;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上,数字图书馆成为一个讨论专题;1997年“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项目”由文化部向国家计委立项,成为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6家重要公共图书馆参与其中;1998年在国家科技部的支持和协调下,国家863计划智能计算机系统主题专家组设立了数字图书馆重点项目——“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同年10月,国家文化部与国家图书馆共同启动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并于第二年完成了“数字图书馆试验演示系统”的开发。成立后的国家图书馆文献数字化中心,扫描年产量3000万页以上。
“数字图书馆”即数字化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系统,具有资源数字化、流通网络化、管理自动化、资源共享化等基本特征。简单来说,数字图书馆就像是没有围墙的图书馆,海量的电子化信息的仓储空间,能让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用户通过网络即时访问、获取信息。
从藏书楼、公共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图书的永恒属性不曾改变,在“云端”继续为人们提供更多智慧服务。(原标题:图书馆蕴藏古今秘密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