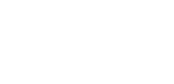导读: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讨论中国文学的价值,应建立在中国文学是否构成对中国现代性创生过程的有效回应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而不是进行抽象和教条的言说。
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已经结束了,但由这次书展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学的讨论还在继续。
这次书展,中国作为主宾国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共有150多名作家参加。与国内媒体的一片叫好声相反,德国媒体对中国文学军团的负面报道占了主流。这大概与德国汉学家顾彬在德国汉学界的权威地位有关,顾彬一直极力贬低中国当代文学。对于外界的指责,当代文学元老王蒙积极回应,道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针对王蒙的观点,《羊城晚报》辟专版进行讨论,讨论未息之时,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与德国汉学家顾彬等人发生争论,争论中陈晓明提出:“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到底该如何评价中国文学的确是个重要的问题。简单地说,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有两种视角:一种是外国人,一种是我们自己。外国人的评价并非都和顾彬一样,顾彬代表了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和无反思的全球化视角。这种简单化的视角本无足论,但他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也触及到中国文学的某些关键问题。顾彬贬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不属于“世界文学”;另一个是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看不懂外文原著,所以是“业余的”。这两个理由合起来无非是说,因为中国当代作家不能好好向西方国家学习,所以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代表的“世界文学”不同。顾彬的浅薄、傲慢不值得理会,但他谈及的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不同倒是讨论中国文学的一个关键点。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和评价也就是围绕着这种不同展开的。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就逐步被纳入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家面对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不同,感到特别焦虑和不安,大家把这种不同普遍理解为“落后”和“差距”。 所以,当时“与世界文学接轨”、向西方文学看齐的声浪空前高涨,这成为当时饱含民族自卑心理和西方中心情结的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于是,模仿、引进西方种种文学思潮、流派的文学现象此起彼伏,用文学界的话说,“我们用几年的时间把西方一百年的文学演练了一遍”。
实际上,这种对文学的理解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长久以来,人们对现代性有这样一种理解,即认为现代性是唯一的、凝固的、模板化的、可以复制的。按照这种理解,中国这种后发国家要进入现代,只有复制在西方国家已经凝固下来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现代性模式。这为历史上的“全盘西化”和当今“与世界接轨”的思路提供了依据。
但是,中国这种后发国家进入现代、获得现代性的过程与西方很不一样,这些国家生成的现代性模式也很不相同,这种不同既是指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也是指后发国家之间也有区别。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来看,现代性不是唯一的和凝固的,而是具有在不断变动中的多样性和创造性。所以,并不存在一个现代性的通用模板可供所有国家复制。与其说中国的现代性是个一劳永逸的结果,不如说是一个不断流动创生的过程。当然,这种流动并非是始终匀速的流动,而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表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特征。
文学作为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自然也就构成对中国现代性创生过程的一种回应。既然中国是经由革命、经由对西方现代性的抵抗和对其危机的克服而进入现代,既然革命的现代性使得中国产生了与西方国家不相同的现代性模式,那么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不同是顺理成章并且具有正面启示意义的。所以,讨论中国文学的价值,讨论是否“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应该建立在对多样现代性的认知和中国文学是否构成对中国现代性创生过程的有效回应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而不是脱离这个基础,进行抽象和教条的言说。